此外,北京医院临床呼吸生理实验室是国内最早进行运动肺功能检测的单位之一。该实验室团队通过对健康成年人以及肺间质纤维化、结节病、陈旧性肺结核、肺叶切除术、肥胖、支气管哮喘、慢性阻塞性气道疾病等患者的长期(6~27年)肺功能随访,了解健康人及上述疾病患者肺功能随增龄变化及其与疾病发展的关系。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先后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三等奖1项及中华医学科技奖三等奖1项。
慢阻肺治疗:从无药可医到可控可治
进入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除了仍对疫情防控不能掉以轻心外,北京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也逐渐恢复了正常的诊疗秩序。郭岩斐惊喜地发现,门诊中人数最多的慢阻肺患者发生了变化:慢阻肺急性加重发病率明显下降,患者就诊数量也大幅度下降。“这可能得益于大家开始戴口罩的习惯,以及‘慢病可开三个月长处方’政策的实施。”
因其早期发病隐匿,慢阻肺一直被称为“沉默的杀手”,是世界第三大致死疾病。据2010年全球疾病负担数据显示,慢阻肺在全球的患病人数已达到3.84亿,占总人口的11.7%。CPH(中国肺健康)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慢阻肺患病率为8.6%,年龄≥40岁人群慢阻肺流行率显著高于20~39岁人群(13.7% vs 2.1%),全国总患病人数接近1亿。郭岩斐清晰地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公众对慢阻肺的认识非常浅显,对慢阻肺的危害重视程度远远不够,常常认为这是“老慢支”,医务人员对慢阻肺的重视也有待提高。在十多年前,也缺少有效的医疗武器,治疗慢阻肺的药物可用“匮乏”一词来形容,而该病患病率高、病死率高、疾病负担重,患者在疾病的急性加重期更是痛苦异常。
如今,大家都认同并且熟知,肺功能检查是诊断慢阻肺的“金标准”。而在20年前,肺功能检查仪器并未普及,有些医院买了肺功能仪,但会用的医护人员很少,有些医生认为用这个仪器费时、费力、费神。郭岩斐说:“当时,最简单的方法是把蜡烛放在离患者二三十厘米的地方,让患者去吹,如果不能吹灭蜡烛,说明患者气流受限严重。”如此简易的方法,放在今天来看可能有些随意,但当时确实如此。最让她难忘的是,慢阻肺重度急性加重期患者所遭受的痛苦。著名相声演员李文华当时患有喉癌合并慢阻肺,虽然生活质量很不好,仍顽强地去面对各种急性加重症状,当时治疗慢阻肺药物有限,李文华最后仍是不治离世。
一位70多岁的淳朴工人,患有重度慢阻肺合并呼吸衰竭,正常的二氧化碳分压在35~45毫米汞柱,他则高到120毫米汞柱,合并有严重的肺动脉高压、右心功能衰竭、液体潴留等,导致全身浮肿。护士给他打针时,针眼甚至会往外渗液。针一拔出来,浅静脉的输液处都在渗液。他做过两次气管插管,整个人的状态很不好,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第三次还要进行气管插管时,患者跟郭岩斐说:“郭大夫,我真不想再受这个罪了,我不要再插管,你让我这么离开就行了”,那揪心的一幕至今仍停留在她的脑海里。
令人欣慰的是,在钟南山院士、王辰院士的带领下,近五年来,慢阻肺的知晓率得到了飞速的提升,无论是医务人员还是大众都对慢阻肺的认识不断增加,重视程度也在慢慢提升。2014年,慢阻肺首次被纳入国家慢病监测体系;2015年,慢性呼吸疾病被纳入国家慢病中长期防治规划;2016年,慢阻肺被列入第二批分级诊疗试点疾病,从国家层面上促进基层慢性呼吸疾病防治。与此同时,慢阻肺诊疗方案也在不断发展,治疗慢阻肺的药物越来越多,“有效武器”越来越多,患者生存质量也迈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可以说,在发达的城市和地区,病情危重的患者已经越来越少。郭岩斐介绍,十多年前,当她还在做住院医师时发现,当时确诊的慢阻肺患者只有两种方法可减缓疾病的发展:第一是戒烟,第二是氧疗,但氧疗有严格的指征,不能随便使用。后来,慢阻肺治疗开始走向了个性化的发展道路。尤其在2011年左右,慢阻肺个性化诊治有了非常大的飞跃,患者诊断不仅要看肺功能,还要对呼吸道症状等各种指标进行分组,不同分组的患者给予针对性的治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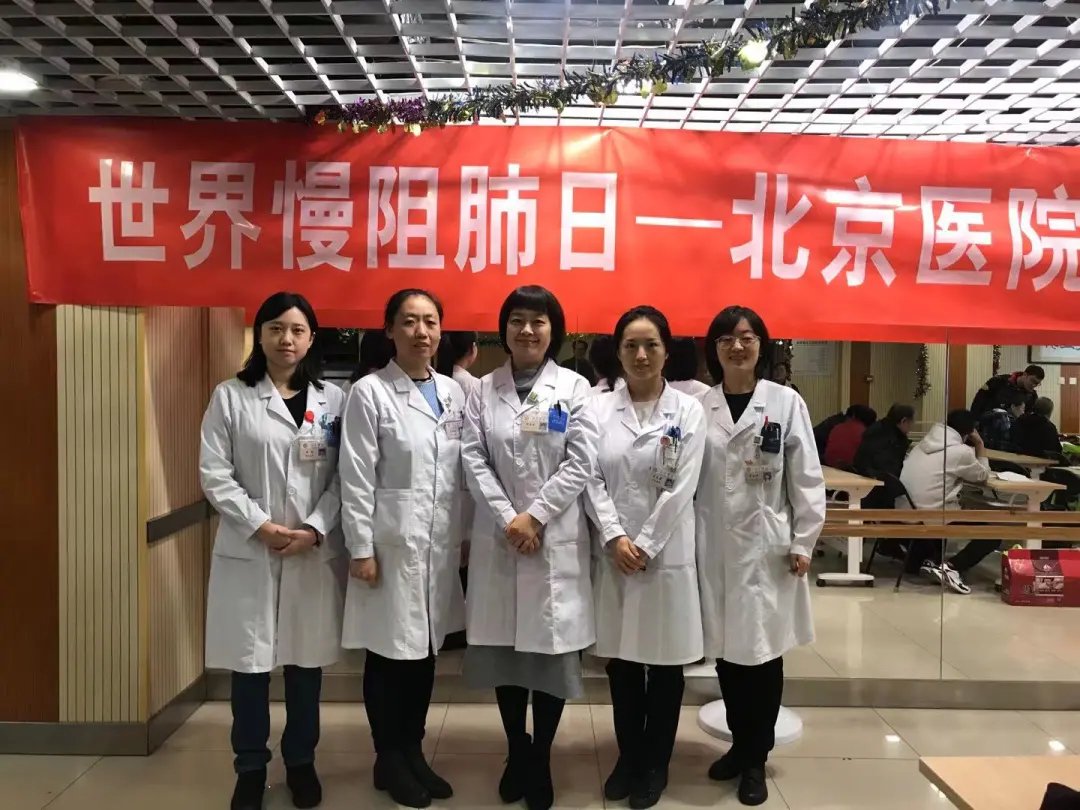
文章插图
现在慢阻肺治疗手段不断创新,比如药物已经出现了“三联吸入制剂”,还被纳入了国家医保目录,进一步降低了患者的疾病负担,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给慢阻肺患者带来了更多的获益。
但在并不发达的偏远地区,如西藏、新疆等地,由于医疗条件有限,郭岩斐还是能看到很多病情比较严重的慢阻肺患者。
- 东莞康华医院|年会聚餐挂横幅:“手术室里全是钱!”东莞康华医院:内容确实不妥
- 院工会|宝鸡市人民医院院工会开展“喜迎新春送祝福”活动 ——传递年味 送去祝福
- 科室|桂林中医院:开展6S管理评比验收活动
- 张仲景|南阳市中医院举行医圣张仲景雕像揭幕仪式
-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平度院区解见业:全科医学科都可以看什么病,你知道吗?|医学科普| 青岛市科技局
- 朱晒红|医院召开迎新春护士长座谈会
- 天津市南开区中医医院|全国巾帼文明岗——天津市南开区中医医院糖尿病科
- 中医医院|澄城县中医医院举行医圣张仲景雕像落成揭幕仪式
- 剥除术|市第二医院完成一例单孔腹腔镜下较大卵巢囊肿剥除术
- 遂昌县人民医院2022年春节假期工作安排|重要通知 | 休息初四
